

旅人:48小时游记 第七季
一个穿着芥末黄灯芯绒西装、顶着蓬松爆炸头的英国男人,正站在苏黎世的街头,他没有忙着赞叹阿尔卑斯山的壮丽,而是在极其精准地盯着手表,计算如何用最快速度吃掉一块当地巧克力。这就是理查德·艾欧阿德,一个把旅行拍成反讽艺术的怪才。在《旅人:48小时游记》第七季里,他继续践行着那个近乎偏执的信条: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城市只要待够四十八小时就足够了,多一秒都是对生命的虚度。 这一季的足迹跨越了苏黎世的精密、伊维萨岛的狂欢、卢布尔雅那的静谧以及米兰的时尚。理查德带去的旅伴可不是什么温顺的游客,从毒舌的李·麦克到冷面笑匠罗伯特·韦伯,这群英国喜剧界的半壁江山凑在一起,硬是把原本高大上的欧洲游变成了充满尴尬、吐槽和冷幽默的生存挑战。他们会去体验最奇葩的当地项目,住进设计感拉满但也可能让人手足无措的酒店,然后在每一个著名景点面前露出那种“就这?”的怀疑表情。 你会看到他们在伊维萨岛试图寻找除了派对以外的意义,或者在米兰的时尚洪流中努力保持自己那份笨拙的尊严。这不只是一场关于目的地的探索,更像是一次次关于“如何在最短时间内高效社交并全身而退”的社交实验。每一个转角都有意想不到的冷笑话,每一顿大餐都伴随着对物价的无情嘲讽,这种极其克制又充满张力的节奏,让原本枯燥的观光变得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脱口秀。
剧情简介
一个穿着芥末黄灯芯绒西装、顶着蓬松爆炸头的英国男人,正站在苏黎世的街头,他没有忙着赞叹阿尔卑斯山的壮丽,而是在极其精准地盯着手表,计算如何用最快速度吃掉一块当地巧克力。这就是理查德·艾欧阿德,一个把旅行拍成反讽艺术的怪才。在《旅人:48小时游记》第七季里,他继续践行着那个近乎偏执的信条: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城市只要待够四十八小时就足够了,多一秒都是对生命的虚度。 这一季的足迹跨越了苏黎世的精密、伊维萨岛的狂欢、卢布尔雅那的静谧以及米兰的时尚。理查德带去的旅伴可不是什么温顺的游客,从毒舌的李·麦克到冷面笑匠罗伯特·韦伯,这群英国喜剧界的半壁江山凑在一起,硬是把原本高大上的欧洲游变成了充满尴尬、吐槽和冷幽默的生存挑战。他们会去体验最奇葩的当地项目,住进设计感拉满但也可能让人手足无措的酒店,然后在每一个著名景点面前露出那种“就这?”的怀疑表情。 你会看到他们在伊维萨岛试图寻找除了派对以外的意义,或者在米兰的时尚洪流中努力保持自己那份笨拙的尊严。这不只是一场关于目的地的探索,更像是一次次关于“如何在最短时间内高效社交并全身而退”的社交实验。每一个转角都有意想不到的冷笑话,每一顿大餐都伴随着对物价的无情嘲讽,这种极其克制又充满张力的节奏,让原本枯燥的观光变得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脱口秀。
观影点评
这绝对是一部拍给那些讨厌传统旅游节目的人看的宝藏。它彻底撕掉了那种充满滤镜的、虚伪的“岁月静好”,用一种近乎残酷的诚实告诉我们:旅行有时候就是很累、很贵,而且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尴尬。理查德那种干涩、克制又带着点社交恐惧的英式幽默,就像是在一杯浓郁的意式浓缩里加了一颗跳跳糖,总能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炸开一个令人捧腹的笑点。 最让人着迷的是节目那种极其考究的视觉美学。每一帧画面的构图、色彩的搭配,都讲究得像是韦斯·安德森的电影分镜,这种极度舒适的工业美感与嘉宾们满嘴跑火车的吐槽形成了绝妙的反差。看着这群平日里才华横溢的喜剧人在异国他乡遭遇各种“小确丧”,你会突然释怀:原来旅行的真谛不在于你打卡了多少名胜,而在于你如何带着一身怪癖与这个世界周旋。 如果你厌倦了那些教你如何寻找自我的治愈系游记,那么这一季节目会让你爽到天灵盖。它不兜售梦想,只兜售快乐和那种“谢天谢地四十八小时终于到了”的解脱感。这种充满智慧的快节奏短途游,简直是当代都市人最完美的电子榨菜,让你在短短几十分钟里,跟着这群有趣的灵魂,完成一场精神上的逃离。


 0
0 0
0 0
0 0
0 0
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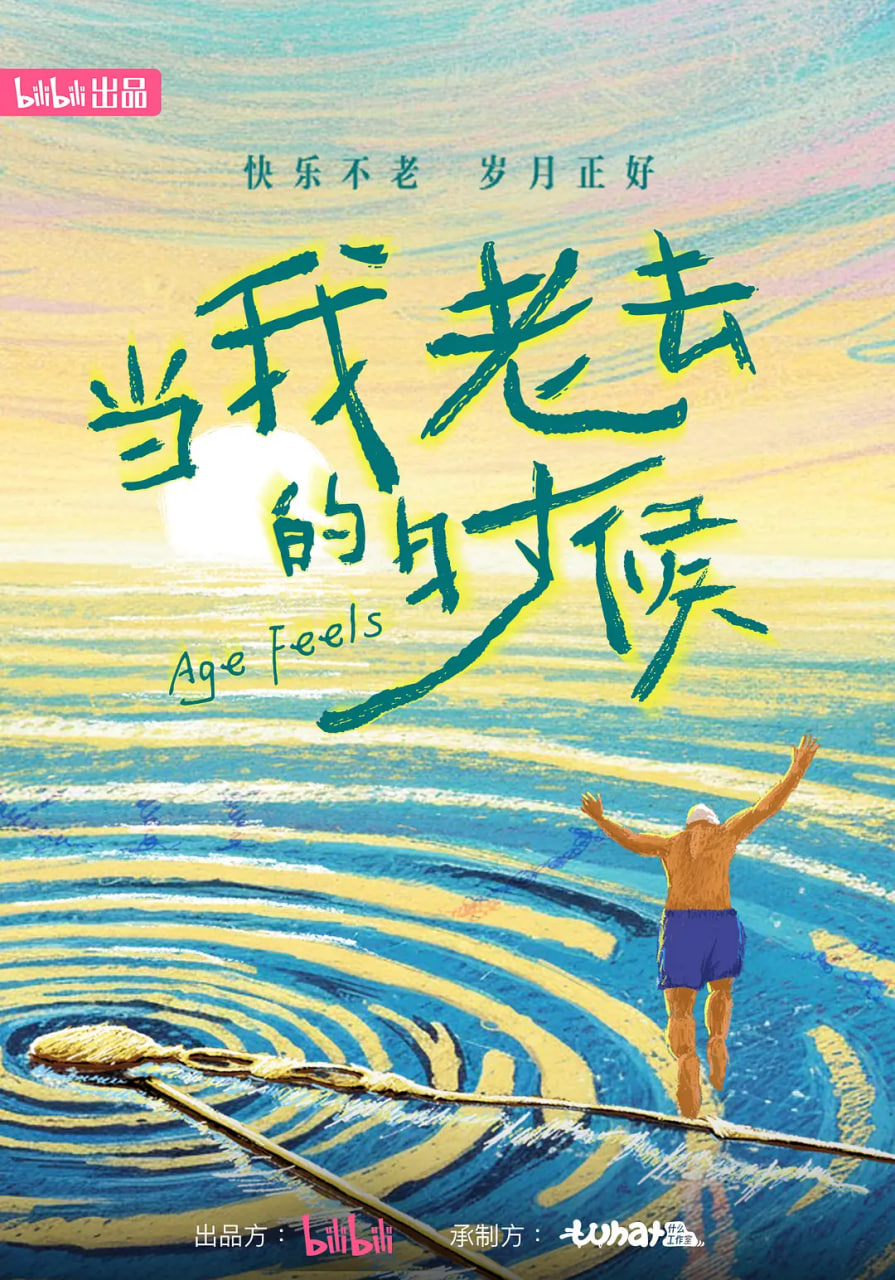 0
0